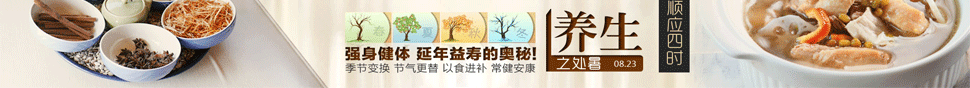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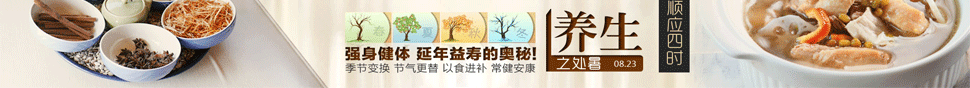
图片来自网络
这年春,他在族叔任元成的长工双喜的指导下,学会了摇耧种地。这是种庄稼中的高级技术,先要定籽眼,用一块破纸撕一个小孔后塞在耧斗里,以孔的大小控制所播种籽的多少,孔大了苗稠,孔小了则苗稀。这一技术的掌握,标志着这个16岁的青年,已经是一个够格的农民,他欣喜异常。夏天锄地的时候,由于烈日曝晒,他的皮肤成了酱紫色。庄稼的长势也很好。可惜,就在丰收在望的时候,一场严霜过早来临,庄稼在籽粒结到一半时全部被冻死,两顷地只收到八九石二流秕谷子。秋收时,他父亲也从大喇嘛营子来到这里,父子们每餐只能吃这些“冻死鬼”粮食。天灾不算,紧接着又来了人祸。直奉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冯玉祥部队的散兵往庄稼地里到处扔枪,真正的农民不敢拾一支。但在土匪的裹挟下,一些遭了天灾的后生拣上枪支就当了土匪,致使匪祸到处蔓延。不得已,他和父亲便背了些粮食到深山里去躲避。这里住着许多蒙古人,他们非常忠厚,父子俩经常用粮食换他们的牛羊肉、奶酪、奶茶。晚间,父子二人就在石檐缝下铺些干草睡觉。就这样,熬了一个多月,冬季将要来临时土匪走了。他们收拾上东西,赶着牛回到了他们的根据地大喇嘛营子。这一年,他可以回老家过年了。他们卖掉了两条小牛,用两条大牛拉着一辆牛车回到了家乡。他离开老家已经两年,虽然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妈妈,但还有曾经养育过他的外祖母。何况,后山的日子简直就是流放和充军,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一个尽头。但回到家乡后,却一点也不比口外轻松。整整一个冬天,他没有在家睡过几个觉。他和虎哥担负了到30里外的火山拉炭的任务。仅仅是自家烧,能用了几车?主要是为了“经商”卖钱,每卖一车可以赚一块银币。父亲为了发家致富,可谓动尽了脑子,想尽了办法,但这也给子良弟兄带来了吃不完的苦。每天太阳落山前他和虎哥便吃了饭,擦黑时赶车出发,一条牛拉空车,另一条牛拴在车后,预备拉上炭时两牛驾车。他们坐在车厢里,上面铺一些糜草。冬天的夜晚很冷,每走一段,就得停下车燃着糜草烤一阵儿火,然后再出发。到了煤窑正是夜半时分,他们把牛拴好喂上草,自己就得下煤窑去了。他们拉炭的地方名叫“火山”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云:“河曲县火山在县西北(指旧县城)五华里,黄河东岸。上有孔,以草投孔中,烟焰上发,可熟食。”“火山”一词,盖源于此。有据可考的时间在北宋,因太平兴国八年即在此建“火山军”。上述烟焰现象,系因煤炭氧化自燃而引起。这一带煤层极浅,手工所采煤炭均在局部露头地带,开采范围小,遇水即另开窑口,所遗采空区也不充填,久经暴露,易于氧化自燃。山名火山,窑名火窑,是一个高温酷热的煤矿。一年四季,矿工们一丝不挂,仍然挥汗如雨。除了热,他们所受的苦也是人间罕见。煤窑多为斜进,巷道高宽各4尺左右,矿工们手拄一尺长的“窑拐子”,背负1米长的窑扁担,前担笸篮后系箩头,腰背压弯成弓,伛偻而行,每担约担斤左右。年长日久,背臀部老茧坚硬如铁。清道光本《河曲县志采遗》记曰:“河曲近塞苦寒而山产石炭。穴而入之谓之炭窑,窑口仅容人行其中,洞狭浅深因人力为之。砍炭者持斧镢入窑,伐以猛力,铁石相击之声日夜不息。置炭于箩,负担者伛偻而行,出诸窑外。窑初入甚浅,后乃渐深,极深可至数里。结伴而入,分坎而伐,日久则面目黧黑,见者呼为窑黑子。盖力作之苦,未有甚于此者也。”又云:“近窑之民,每岁农事毕,冬无营作,则入窑砍炭。窑工自叹曰:‘人言地狱受苦,炭窑即活地狱也。寝食其中,不见天日,血汗淋漓,渍以煤垢,形状如鬼。使吾力穑逢年,足以糊口,顾肯劳动如是耶?’”子良和虎哥下煤窑,一是为了帮矿工把炭车子推出来。因这个窑近窑口一段可用独轮的推车,但洞狭车重,须得有人在后面推着方可出来。他们的一辆牛车可装两小推车炭,约0斤。如果感到不足,还可自己下窑去背,这个不算钱;他们背一次,又可增加斤左右的炭。这就是他们下窑的第二个“意义”。装好车以后,他们就伴着满天的星星踏上归程。图片来自网络
在火窑子稍北,县府设有一个税卡,每车炭须纳8个大铜板的税,他们停下车,把铜板递进去。其实在黑洞洞的夜里税员根本不敢出来,他们怕拉炭人把他们揍死,就这样子良他们也从未偷过税。天快亮的时候,炭车到了石梯子村下封冻了的黄河边上。这里离家还有十几里路。人困牛乏,饥寒交迫。定睛一看,两个人皮帽的边沿上都结满了白色的冰霜,眉毛、头发雪白,上下眼皮粘到一起,简直象个“圣诞老人”。再看“牛王爷”,拉着沉重的炭车不住地喘气,眼睛和面部也都成了白色,嘴边还挂着几寸长的冰锥。他们多么盼望快点回到自己的家门口!当太阳一竿高的时候,他们真的到家了!但还不能喘歇,他们必须把这1多斤炭从大门外一块一块或一筐一筐地搬进炭场,垒齐垒好,才能回家吃饭,然后美美地睡三四个小时。下午起来,又是铡草、喂牛、饮牛……当太阳下山的时候,他们这一对难兄难弟,就又赶着牛车开始下一个难熬的夜晚。如此周而复始地干了一段,父亲也看出孩子们太苦,于是改变方式,将二套牛车改为一头牛的单车,赶车也改为隔天轮流单人去赶,这样牛和人都得到了休息。他们拉回的炭,大部分卖给了本村的人,每车可卖两块银元,获利颇丰。但这种不要命的劳作,确实令他心力交瘁。唯一的好处,是锤炼了他不怕任何困难的顽强意志。但是,大喇嘛营子才是他家衣食的根本。年春天,他们原班人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走西口。春去冬回,这已是河曲县走西口者固定的公式。一样的黄牛,一样的牛车……所不同的是,由于头年霜冻造成的失败,父亲今年放弃了后山大榆树滩两顷租种的地,一门心思经营大喇嘛营子的自有土地。这样,子良就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地去“充军”了。这里人多,红火,纵然受苦,也觉得快活。此时他和虎哥俱已成为好劳力,父亲因给人看病,已变成了辅助劳力。继母给他们做饭。这一年中秋之夜,过得非常热闹,人们吃过饺子、月饼、西瓜、毛豆角、煮玉米之后,都去睡觉了。洪涛爷当晚也吃得不少,但很少说话。第二天早晨起来,人们发现这个向来起得最早的老人还无动静,就去看,结果发现老人已在一个放草的房间里悬梁自尽,终年72岁。可怜的老人,与他们患难多年,今日竟不辞而别!他大约是不想再拖累别人,才选择了这条路。其实,他们何尝在乎他吃的那点粮食?而且,人们在躲土匪、回河曲的时候,这个失明的老人是唯一可以留下来看门、喂狗的人,他的贡献有目共睹。然而,谁又能理解这孤独老人内心的痛苦?他们含着眼泪,将老人葬在了他生前居住的“伙房”东南的沙梁上。从此这里又少了一个人。年是个平年。农历十月,他们赶着两条牛、一头驴、一辆车,又回到了老家河曲。冬季除了照旧打夜班拉炭外,又多了一项下南山驮粮的任务。他父亲在距巡镇百里的阴塔村买下约0斤糜子,山高路远,每4天才能驮一回,每回驮多斤,前前后后跑了6回,用了24天。卖粮的人叫苗学明,是他高小时的同学,一个十足的小财主,此公架子很大,认钱不认人,没有一点同学的感情,一副为富不仁的脸孔。从家中去阴塔路过他大姑妈嫁过去的村子郭家庄,离河北30里,每次来回他都要在大姑家中住一夜。大姑总要给他吃一顿面食。冬去春来,年,他们又照样口里口外奔忙着。值得一提的是,子良在这一年学会了盖房。因为他们一家孤独住在野外,所以难逃土匪的侵扰,于是他父亲下决心在离这里十几里外的东社买了一块地皮,要盖几间土木结构的房子。因东社人口较多,又有“社”,土匪来了比较好应付。夏初开始,子良一个人被派去脱土坯。开始每天只能脱多个,以后逐渐增加到个。他脱的土坯全部是水坯,其工序是:先把泥土铲好,浇上水,搅拌成稠泥浆;然后把坯模放好,坯模是用木料制成的带底的两个长方形格子,每格比砖头略大;再将泥用双手挖着放进坯模里,多余的泥再用两手刮平;最后将坯模端起倒扣到一个干净平坦的地方,将坯模拔起。干了以后便是很好的土坯。蒙古草原煤炭奇缺,根本烧不成砖,房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坯房。正式盖房的时候,他的父亲和虎哥都来了。他们先用土坯砌墙,砌时将门、窗的框子筑进去,然后立柱、上梁、压栈、清扫,房子就算盖成了。所用的梁、檩、椽、栈等木料,都是大喇嘛营子自栽的柳树。从14岁失学至此,口里口外,子良已当了5年农民。其中西口外的苦难,就受了4年多。他当过佃农,当过自耕农,饱尝了旧中国农民的艰难与辛酸。他看不到光明。再这样受下去,累死累活不说,连维持较好的家庭生活都不可能。“挣钱不受苦,受苦不挣钱”,难道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吗?他开始考虑如何摆脱这没完没了的困境。任子良的叔父在归绥上学。多年以来,这个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他的身上,故此在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。年夏天,他的叔父从绥远中山学院文史专修科毕了业,并且在省府的什么机关找到了工作。家庭的负担减轻了,但叔父对家庭则不愿承担经济上的责任。子良对此大惑不解:我们累死累活供他上学,他为什么不帮我们?他要去找叔父,求他在归绥给他找一个哪怕是“工友”的工作,逃脱这累死累活永无出头之日的苦海。他把这想法和祖父、父亲说了,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他便整理行装,孤单一人,又一次踏上了走西口的漫漫征途。70多岁的老祖父将这个从小没娘受尽苦难的孙儿送到了村外,挥泪而别。他身挎一个简单的行李包,晓行夜宿,赶往归绥。只身进入库布其大沙漠后,他害怕极了。茫茫沙海之中,根本没有路,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,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中探索前进。一旦迷路,就有倒毙的危险。人们视其为西口路上的“鬼门关”,有的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“离门纸”,然后才进入沙漠。大部分的人,则是结伴或随驼队而行。他这样冒险,能活着走出沙漠,实属侥幸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数次乘牛车走口外的经验。整整走了7天,他终于到了归绥。一见面,叔父就问他:“你来做什么?”他以实相告,不想叔父冷笑着说:“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事情干,你能干什么?”一口一个“找不到”,像一瓢凉水浇下来,直透他的全身。叔父给他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,他想:你神气什么?还不是靠我们父子供养的你?这会儿,反正缠也缠住你啦,我就是不走,看你怎么打发?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学生忙着上学、下学,心想:自己要是能够上学该有多好!子良的这股牛劲令叔父毫无办法,他只好答应让子良上学,却又说:“你过去学的一些东西都忘记了,要上学,还得先补习一下。”于是便找到了土默特旗中学附属小学,跟了一个六年级班,进行补习,暑假毕业时正好参加初中和初师的升学考试。这是年农历二月间的事,此时他已19岁。初进班的时候,感到非常吃力,因为5年的艰苦劳作,已把过去学下的好多知识都忘记了,特别是算术和英语。他废寝忘食地加倍努力。同班有一名河北宝坻县来的学生,叫韩宝祥,功课很好,他便有意接近韩,和韩交上了朋友,处处虚心向人家请教。4个月后暑假毕业考试,他居然考了全班第一。正当他准备利用暑假复习并参加中考时,他的叔父却提出了一个令他十分伤心的问题:叫他回河曲接家眷。这无非是怕考上学校又要连累他花钱,否则为什么不迟不早,偏要在他正准备中考时急着去接老婆孩子?但既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?他含着眼泪,又一次踏上了回河曲的征程。在当代人看来,呼市到河曲多里地真算不了什么;但那时是一步一步走,就是神仙也犯愁。当时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从归绥经托克托县的河口镇过黄河,沿准格尔旗的九枝榆树沟、黑岱沟,大饭铺、十里长滩、马栅,再过黄河,才是河曲的土地家湾(河湾)、大东梁……才能到家;另一条路是从归绥出发,经和林格尔县、清水河县,到偏关城,回到河曲石城村再回家。他选择了后一条路,这条路不需要渡黄河。出发后的第六天,他走到了偏关县城以东的一个山梁上,忽然之间雷雨交加,尽管他带了一把雨伞,但在大风之中根本无用。他浑身湿透,好不容易下了坡,到了关河口。关河不算小,又没有渡桥,看着水不太深,他就冒冒失失地淌水过河。走到离对岸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,一个大浪打来,将他裹入洪峰,向下游冲去。他拼命挣扎,慌恐之中,像有神助的一般,脚下竟踩住了泥底,爬到了对岸。这是一次几乎丢掉性命的遭遇。附近没有一个人,他将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拧干再穿上。走了一阵,就到了偏关县城,但天色尚早,他不敢歇脚,继续前行,赶太阳下山以后,回到了河曲境内的石城村,住了下来。这里离他的家乡只剩下了一天的路程了。回家后住了几天,他便接了婶母和三岁的堂妹坤弼,再返归绥。这次走的是又一条路,从土地家湾过黄河,住在一个朋友阎治国的家中,托阎雇了高万和的三头毛驴,两头驮一个绑好的“驾窝”让婶母和坤弼坐,一头他自己骑。这自然比步行轻松多了。但想不到的是,在河口镇的黄河岸边,他们又遇了一次险:一头毛驴陷入泥潭,越陷越深,眼看不行了……多亏岸上的乡亲们全力救助,才把驴救上来。到了归绥,叔父一家欢欢喜喜住进了租好的房子,而子良却误过了初级师范的招生考试日期。他十分懊丧。经再三哀求,校方才准于补考,但结果仍旧未被录取。他猜想,这是校方为了安慰他而采取的一种“计策”,以他的成绩,他怎么连个初师也考不上呢?好在还有绥远第一中学没有招生。他果断报名,果然就被录取了!但使人发愁的是:学生入学必须交10元钱,逾期不交则除名。他向叔父要钱,叔父竟冷冷地说:“没有钱,你还是回去劳动吧!”他一分钱也不给,想的是快快把这个侄子打发走,免得成了他经济上的包袱,这样也就遂了婶母的心意。想起自己多年来所受的苦,子良伤心透了。但他绝不能回头!眼看交学费的限期越来越近,他毫无办法。再求叔父,还是不给钱,而父亲又远在“天边”。他横了横心,向一个叫黄宝琨的河曲老乡借了5元钱,急急忙忙跑到学校。一到学校,正好碰到学校的工友乌文升正拿着一纸通告要去贴,上写:新生任子良等至今尚未交来学费,着即除名,以备取生递补。他向乌文升哀告,求他暂不要贴,他现在就去交学费。乌是一个好心人,当即答应:“你快去交,我等你。”他赶紧跑到教务室,一位老师正在那里办公,后来知道那是位美术教师,叫佟公超。他向佟鞠了一个躬,说:“我来交学费。”说着拿出那5块钱交给佟。佟说:“学费是10元。”他慌忙解释说:“我现在仅有5元,剩下的5元容我以后再交。”佟说:“那不行,要不你去找校长。”他抱着一线希望,找到了校长冯光荣。冯是河北省人,身材高大魁梧,50开外年纪。冯开始说不行,经他再三哀告,说明他是外地来投考的学生,近日吃饭都很困难,请容缓交,一个星期以后一定交清。校长最后答应了,告诉会计先收下,并叮嘱他一个星期以后一定要交清。他满口答应,带着感激的心情深深向校长鞠了一躬退了出来,就像被死神夺去性命的人又回到人间,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一个星期后,会计催要所欠5元学费,他说还没寄来,请再宽限。这样人家一再催欠,他一再请求宽限。几个星期过去了,还是无法偿还。不久学校闹起了学潮,本地势力排挤外地人,正直的冯校长被赶走,换来一个新校长叫班浩,像猴子般瘦小。他所欠的5元学费也就没有人再催要,直到初中毕业,也没有补交上去。他深感内疚,但有什么办法呢?父亲经济极度困难,叔父又不肯帮忙。但他并未忘却,一直把这愧疚藏在心里。直到5年这所学校(后更名为呼市一中)百年校庆时,已经96岁高龄的他给学校寄去元钱,并郑重其事附了说明信,说他永远难忘第二故乡,难忘母校,但这元不是捐款,也不是赞助,是想赶在自己有生之年还上那欠了足足70多年的5元学费。他说,5元再加70年利息,足有元了。是的,他从草原学到的不少,欠帐也可以说很多。了此心愿第二年,老人就与世长辞了,这是后话。(未完待续)周少唧,山西河曲人,生于年10月。年毕业于省立山西五寨师范学校。年以自学考取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凭。年参加工作,先后任小学中学教师,教育局视导员,县委办公室干事、副主任兼秘书办公室主任,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(《河曲县志》总纂),县政协秘书长、河曲中学校长、县委调研员等职。4年退休。中国地方志学会会员,被收录入《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》,副编审。
已出版著作共余万字。主要有《河曲县志》《河曲县志资料》(以上均为年版)《九十行过》(任子良传),《增广写信必读》(校注)《河曲建设志》《河曲县地名录》《巡中校志》《河医院志》,《王海元》《贺章甫》(纪念文集)。个人散文集《怀旧录》。
感谢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donglingcaoa.com/dlctx/8845.html


